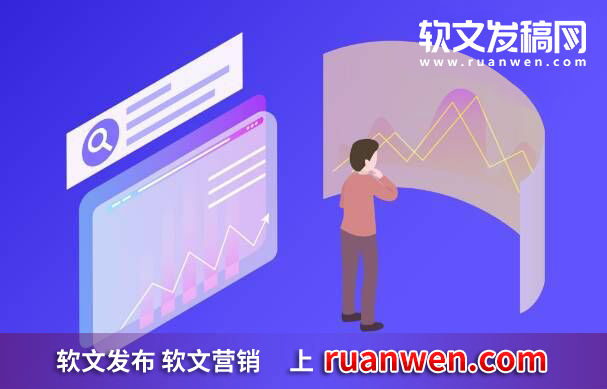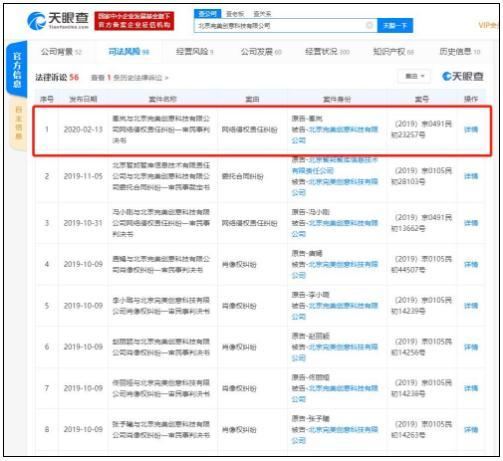一个自闭症家庭的19年:最怕听到别人说这孩子真没教养
“最怕听到别人说‘这孩子真没教养’,其实我们花的功夫成千上万倍”
熬过崩溃,比现实更焦虑的是未来,抱团取暖是他们的渴望
一个自闭症家庭的19年
本报记者 杨茜 文/摄
因为疑似自闭症,6岁男孩乐乐被妈妈小叶遗弃在了杭州城站肯德基店(钱江晚报、浙江24小时APP近日曾做连续报道)。
乐乐和小叶的故事经钱江晚报、浙江24小时APP报道后,不少和小叶同病相怜的家庭给我们打来了电话。每个自闭症家庭,都经历过小叶的崩溃和绝望。只是,大多数人最后接受现实,并选择让自己强大。
47岁的吴民(化名)是杭州一家小便利店的老板,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一个19岁患有自闭症的大男孩的父亲。近日,钱报记者走近吴家,记录下这个家庭的日常。
下午3点40分,是晨晨(化名)放学的时间。一到点,他会站在杭州杨绫子学校的门口,等爸爸来接。
学校边上的“智慧树”小店,晨晨盯着各式蛋糕看,没有吭声。吴民看出儿子眼中的渴望:“想吃哪一个,就自己去买。”
晨晨兴奋地到收银台边,掏出手机,点开支付宝,“哔”地一声支付成功。
记者夸晨晨很棒的时候,吴民说,只有回过头来想想的时候,才会发现迈出的这一步是有多大。
那一刻,即使有心理准备
但依然很难很难相信
19年来,极致的欣喜和痛苦,这个家庭都尝过了。
2000年1月17日,晨晨出生。一对年轻人,初尝父母滋味,有无措,有激动,在孩子的啼哭声和自己的手忙脚乱中,度过了最幸福的一年。
即使当其他孩子开始牙牙学语时,吴民也没有太在意。都说“贵人语迟”,说不定晨晨在某一方面“天赋异禀”呢。事实是,这样的“自欺欺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不堪一击。除了不说话,一岁半的晨晨拒绝眼神交流,连最简单的对视都做不到。
一开始,吴民以为晨晨是聋哑孩子。夫妻俩抱着孩子四处求医,甚至花了2万多元给晨晨配了助听器。
孩子3岁时夫妻俩第一次去北京,在一家脑科权威的医院里,他们得到了自闭症确诊单。那一刻,即使有心理准备,吴民还是感觉像被判了“死刑”。
晨晨低着头一语不发,妻子整天以泪洗面,吴民难受到心里好象有根针在刺。
一边没日没夜地赚钱
一边给儿子做康复训练
接受现实并且熟悉晨晨作为自闭症孩子的一举一动,是他们能做的第一步。
自闭症患者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刻板、规律。晨晨很安静,“专心致志”玩玩具,能连续几个月只玩一个玩具,无论大小,必须随身携带,否则就会从嗓子里发出低吼,开始哭闹。晨晨还会莫名其妙地笑,踮起脚尖转圈圈,直到摔跤……
夫妻俩在杭州市中心开了一家小便利店,离不了人。所以只能一人看店,一人带孩子。
吴民多方打听了解到,自闭症患者需要做康复训练。“根本不去想未来,也没有很远的打算。当时只有一个目标,做训练。”
夫妻俩起早贪黑,延长开店时间,赚钱给儿子做康复。接受现实之后心里的念头只有一个,就是一边赚钱一边给儿子看病。
那年听说美国有种药对自闭症有改善作用,夫妻俩想尽办法找人代购,每个月好几千的药费,让孩子吃了一两年。
晨晨4岁进入康复机构,在杭州待了一年,又去青岛康复了一年。
那么多年过去了,吴民依然记得当晨晨终于喊出那一声“爸爸”时,彼时他内心的激动。他对妻子说,“儿子终于开窍了。”
一遍遍重复和解释,还要应对突发
有时候崩溃起来悄无声息
晨晨在进入杨绫子学校读书后,日子似乎进入了正轨。但这种所谓的“正轨”,并不意味着风平浪静,而是要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还有一遍遍不断的重复和解释。
比如说,小店靠近贴沙河,晨晨又喜欢玩沙子。有一次晨晨独自跑出去,吴民发现后立刻关店,发动大家去找人,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找到。“不像正常孩子,有人喊名字就会有回应。他不会的。”所有人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晨晨回来了,吴民至今都不知道这段时间晨晨去了哪里。
比如说,如果看到别人口袋有东西吸引他的话,晨晨就会伸手去拿。吴民夫妻俩常常要一个劲地道歉、解释。
“最常听到的也是最怕听到的话是‘这孩子真没教养’。”吴民说,事实上,在教孩子方面,他们下的功夫可能是普通父母的成千上万倍。
倒一杯水递出去,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每天重复上百遍地教,晨晨也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以前,吴民工作,唱歌、跳舞、打球,非常活跃。自从有了晨晨,他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每天都在重复这些让人崩溃的日常,一遍遍,已经磨平了岁月与脾气。
吴民说,有时候崩溃起来悄无声息,“周边也有因为自闭症孩子影响夫妻感情,因为孩子而争吵最终家庭破裂的。”
“无论是孩子的异常,屡教不改,还是外界的质疑,这些都是我们所要面对和承担的。有些人脆弱,承受不住,而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变得强大。”吴民觉得自己是后一种人。他说,他们不需要藏着掖着,也不需要同情,需要的是理解和宽容。
如今,晨晨的交流已经没有太多障碍,而且还在学习钢琴、非洲鼓,学会了支付宝付款,消消乐等简单的游戏玩得也很溜。
有人说,自闭症的孩子其实都很聪明,甚至在某一领域是天才。吴民愿意相信儿子晨晨可能就是这样的“宝藏男孩”。
比如晨晨已经将万年历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了。
“1999年7月13日,星期几?”
“星期二。”晨晨回答。
只要答对了,晨晨就会伸出大拇指,想要在对方大拇指上盖章。这是父子间的一种奖励方法。而这样的测试,百发百中,准确无误。
自闭症患者能就业的很少
不能让他待家里,想抱团取暖
戴着鸭舌帽的吴民说着过往,大多数时候一脸坦然。他说没有计算过在晨晨身上的花费和付出,也没有天天指望着晨晨都有进步。只是回头去看走过的那些“一步一脚印”时,无论对于晨晨还是他们自己,都很想说一句“你真的挺棒的”。
但是现实依旧是现实。还有一年时间,晨晨就要从杨绫子学校毕业了。即将走出他的“舒适圈”,他会有怎样的表现,没人知道。
杨绫子学校目前约有学生210名,自闭症孩子占到四分之一。“几年前,每个班级也就一两个自闭症孩子,现在一个班能有五六个。”副校长姚郑芳说,这些孩子从学校毕业后能就业的凤毛麟角。“现在轻度甚至是中度智障的孩子,会被一些企业接纳,做些性质单一的工作,也算是融入社会。但自闭症不一样。有特殊才能的自闭症患者少之又少,除了部分人去工疗站外,更多的自闭症患者无法就业,只能选择居家生活。”
吴民有些焦虑,“我不能让晨晨待在家里,这样只会越来越退化,我和她妈总有一天会离去,到时候怎么办。”
吴民是个实干派。他知道,这个时候只能抱团取暖。他计划着,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家长一起,为自闭症的孩子打造属于他们的“小社会”,里面可以学习、工作、生活,得到24小时的托管。
“这很难,但不是没可能。问题来了就解决,总会实现的吧。”吴民说。
本报记者 杨茜 文/摄
编辑:臧小景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