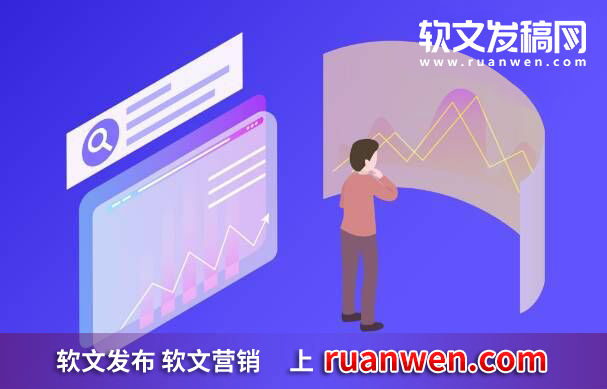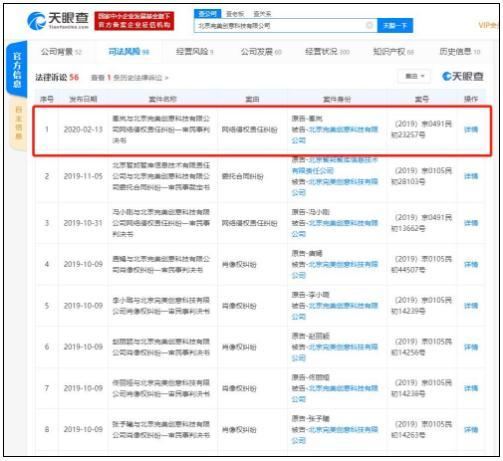环球播报:中国医师节,我们记录了6位广东医生的“医瞬间”
没有人生来就是医者。医者的成长路上,有人动摇、有人放弃,更多的人在不断探索。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他们,从何时开始决定为医学奋斗一生?行医越久,留下的遗憾也就越多,他们是如何从遗憾中获取力量,更好地护佑生命?8月19日是第五个中国医师节,记者采访了6位来自不同医院、不同科室的临床医生,寻找他们医者生涯中的“决定性瞬间”。
穿越生死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你已经有一个孩子了,生命比生育更重要,你不能为了生孩子放弃你自己的生命。”在诊室里,全国名中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儿中心教授罗颂平用上了少有的严肃语气。对面是一位确诊子宫内膜癌的女患者,还不到30岁,医生建议她切除子宫,她却希望保留子宫生下二胎。
罗颂平。
罗颂平常接诊这样的棘手患者。作为全国知名的中医妇科专家,疑难杂症病人都是带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她。在她的帮助下,生命的惊喜也时常降临。
有一位卵巢已经不“工作”的病人仍想怀孕,罗颂平没有信心,只能建议她吃药试试,再搭配膏方、针灸。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一年后病人能排卵了,最终自然受孕,罗颂平全程为她保驾护航,并在2年后又助她怀上二胎。
但从医越久,她觉得遗憾越多:“医生不是万能的,我不是总能帮助她们完成愿望。”其中就包括不少“拼了命”也要生孩子的女性。“我多希望她们在遇到生存和生育的两难时,能为自己多考虑一些,更加爱护自己。”
在生与死的边缘工作久了,总有一些鲜活的病例,能让医生们刷新自己的生命观。
“2013年,我在阿富汗昆都士省做了66天的战地医生。”广州和睦家医院医疗总监、麻醉科医生赵一凡回忆,赴伊拉克前,他在国内一家三甲医院工作,日常主要在手术室内做麻醉;但在阿富汗,麻醉医生要在急诊里抢救危重患者。
他记得很清楚,一个9岁左右女孩的腹部被子弹击中,肠道被打穿,被家人裹在一张红色的毛毯里,流着血奄奄一息。赵一凡和同事们把库存的最后一条中心静脉导管都用上了,团队一起努力了整整两个星期,还是没能救回她。
这段经历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回到国内,赵一凡开始在日常工作之余参与对重症患者的探访和关怀。
赵一凡。
有一个肿瘤恶性程度很高的46岁胆管癌患者,担心3个孩子和80多岁的母亲承受不住,一直不敢直面现实。赵一凡建议他停掉已不能获益的化疗,帮助他管理好癌痛,充分肯定他对家庭的付出。
“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向母亲坦露自己的病情,把想对孩子说的话用手机录下来,还坦然地向太太表达爱和感谢。”赵一凡说,“帮助患者从生命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帮助他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也是医者的使命。参与临终关怀也让我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情。”
记住遗憾
“我爸爸是很倔强的一个人,他觉得医生故意把病情往重了说,就没有遵医嘱治疗,也没有跟我说这个事。”提起往事,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张世忠眼里还是有藏不住的遗憾。2006年,哈尔滨当地医生诊断张世忠父亲的左侧颈总动脉狭窄严重,但没有进行手术介入。
张世忠说,后来父亲突然出现脑部缺血梗塞,从一个能说善写会画的高级工程师,变成失语、失读、失写,右侧肢体偏瘫的人,至今已十余年。
张世忠。
“如果医生能跟爸爸好好沟通,结果可能好很多。”这成为张世忠行医生涯中的一根刺,刺向当年,也刺向自己。从此,他习惯把微信或电话号码留给患者,方便他们直接询问;在门诊,他常常连画图带比划,一定要让患者理解治疗方案。
帕金森患者多半脆弱、固执,一名患者的儿子给张世忠写信,说自己的父亲“对什么事情都不满意,只有张主任能让他接受手术方案”。张世忠读着信,难以抑制地想起父亲。
医者的职业生涯里,难免有遗憾如影随形。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内科门诊主任、发热门诊主任李淑华的记忆里也有这样一根难以忘怀的刺。
大学刚毕业的她在一家医院的儿科当住院医师,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孩因发烧3天来看病,李淑华发现他的嘴唇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鲜艳颜色。
“我提出孩子会不会是川崎病。但上级医生认为,孩子眼睛没有红,嘴唇虽红但没有出现皲裂,与川崎病的诊断标准不符。”李淑华回忆,她的意见被否定了,患儿还是接受了抗感染治疗,2天后因效果不好,家长带患儿去了其他医院,最后确诊了川崎病,针对性治疗后很快痊愈。
李淑华。
“其实也不能说我的上级医生就错了,因为川崎病往往要持续高热5天后才能确诊,当时才是第3天。”20年来,这件事常在李淑华心里敲响警钟,“我由此也学到了重要的一课:面对疾病时,谁都不能凭着资历就能高傲,而是应该时刻保持谦卑。医生一定不能只对照书本来看病,因为患者不会按照书本来生病。”
保持热爱
“1973年,刚读完高中的我回到生产大队,当了一名‘赤脚医生’。”回想最初行医的日子,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核医学科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核医学科带头人蒋宁一仍记忆犹新。
他上过赤脚医生培训班,给几个医生师父背过药箱,消毒、注射不在话下,采药、抓药、针灸、推拿也学了一些,但并不“包治百病”。生产队里有一个老农民,右边小腿胫骨附近有一个伤口,一直溃烂,深的地方能见到骨头,长年累月治不好。蒋宁一帮他消毒、敷草药,伤口有一定的好转,但始终没有愈合。
蒋宁一。
“按现代医学的观点,那种伤口是要植皮的。”蒋宁一回忆,没过几年老农民就去世了,走的时候还带着那个伤口,“村民们的痛苦,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力不从心。觉得自己这个赤脚医生没当好,就很想去读书,想提高医术。”
在蒋宁一当赤脚医生的第5年,1977年,高考恢复了。他马上报名参加复习班,高考成功后被苏州医学院放射医学专业录取,一步步走上研究核医学的道路。
今年蒋宁一已经67岁了,还是有点“停不下来”:当学科带头人,写书,用核医学治疗疤痕、治疗因甲亢导致的眼球突出……他说,就是提高自己的水平,多做一些事、多帮一些人。
想要成为更好的医生,这份热爱驱使无数医者前行。
54岁伍丽(化名)是华南地区首例国产超轻人工心脏临床试验入组患者。一个成人拇指头大小的“泵”,替代了她的心脏泵血功能。术后,原本心衰终末期的她,可以重新大口呼吸,重新自己行走。
为她主刀手术的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外科副主任黄劲松,多年来长期奋战在心脏移植一线。他常说“心脏移植的刀很重,刀下有三条人命”,一是心衰病人的命,二是供体心脏捐献者的命,三是同样在排队等待心脏的另一位病人的命。
黄劲松。
拿稳这把沉重的手术刀,黄劲松花了很多年。“打个比方,你要代表学校参加一场球赛,肯定不是现在才开始训练的,而是对这件事已经热爱了很多年,经过充分的学习、有了一定的能力,才会最终走上赛场。”他说,“我们心脏外科医生,最开始都是从体外循环这样的生命支持技术开始,再慢慢去触碰那个生与死的开关。”
在世界范围内,像伍丽这样长期携带人工心脏生存的患者越来越多,最长的已存活十余年。但在我国,这类实践仍在起步阶段。
“有的病人放过多次支架,到最后心肌都纤维化了,怎么办?心脏移植、人工辅助心脏等新技术为他们带来了希望。”黄劲松说,基于临床需求,医院、科室也会组织技术力量,一步步往深处难处攻坚,“作为医生,如果把个人的职业生涯和团队的发展方向结合在一起,就有机会充分发挥才能,让自己和团队都变得更好,最终让患者受益。”
【统筹】李秀婷
【采写】钟哲黄锦辉朱晓枫 见习记者 陈嵘伟 实习生 吴丽婷
【剪辑】杨奇
关键词: